李宇春:反客为主 之前一点都不喜欢表演
2021-06-27 16:38:41来源:时尚芭莎
我常常会跳出李宇春去看李宇春。
跟李宇春聊天之前,我只提醒了自己一件事,那就是:
2005年已经过去16年了。
01
李宇春曾说过,“歌手”这个称呼,会比“艺人”这个称呼让她更有归属感一点点儿。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不是一个“演员”。
当她开始认真地去作为一个演员之后,或许就连她自己也没有发现,她与“艺人”这个词的粘连更紧了。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开始做演员。
她告诉我,她不是故意的:
我之前一点都不喜欢表演。
十几年前,我刚当歌手的时候,就有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找过我,让我去演戏,但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对于表演,一方面我并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它也不自信,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去参与过。
但是伴随着我的工作与表演这件事所产生的摩擦,比如说参与到一些电影里面的契机等等,我对于表演这件事有了一些从内心深处滋生的改观。更具体地说,它让我有了一种通过挖掘所饰演人物的内心去表达我私人感受的一种兴奋感。
就是我觉得,我找到那个感觉了。
“是在《如梦之梦》中找到的吗?”我问。
《如梦之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在这个话剧里面维持一整年的排练和演出,但我说的这种感觉不是演完马上就找到的,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李宇春并不知道她演的《如梦之梦》我看过。
那是2013年圣诞,在北京,保利剧院。
我进了剧院之后才知道,原来演员名单里还有李宇春。当时我想:哦?李宇春还会演戏?
再后来发生变化就是在《我就是演员》第三季里了。李宇春跟郭涛、杨迪演绎的《无名之辈》,依然称不上成熟,但是我被李宇春以表演的路径打动了。
在那场表演里,平时淡定惯了的李宇春失声痛哭,我知道她是在为角色服务,但我还是想问问她:“你当时的释放,到底是属于角色的,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我觉得是属于我们彼此的。
李宇春迅速地回答: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从表演这件事情中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快感。
因为在《无名之辈》中,我所饰演的马嘉旗那个人物,她内心中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她的孤独和无助嘛,那么,可能我在我职业生涯的前五年、前十年,这种相似的孤独和无助也是时常伴随着我的,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宣泄过。
有的人可能会跟家人朋友去倾诉,但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自我消化和思考之中。
思考与追问,这两个动作,不论是在李宇春过去与其他人的对话中,还是在与我的交流中,被提及的频率都是非常高的。
它是一种找寻吗?还是李宇春天性中不安定因子的一种外化呢?
“似乎一个足够有安全感的人,不会像你这样去进行频繁的探索。”我告诉她我的角度。
她想了一会儿:
我可能没有想过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好像就是会想问,不断地问。
我会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这种好奇心会驱使着我,我是小到去一个综艺节目我也要问为什么的。
“问什么呢?”
比如说,我会问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综艺节目,而不是那个呢?为什么是去参加演员的综艺节目呢?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科班的演员,而且我并没有想过未来在演员的道路上要去有什么发展,为什么这种情况下我要去参加一档演员的竞技类节目呢?
“那答案是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处在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音乐这个载体暂时没有办法让我有多一层的可能性去进行表达;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表演过话剧,我很享受一次性的舞台表演——那种与观众之间的不一样的距离,其实它会比影视表演更吸引我。
在另一个采访中,李宇春讲过一件事。
她说有一次去台湾的夜市,到了之后,出于一种对人群的巨大恐惧,导致她只得不停地往前走,什么都顾不上。
“我后来回来自己想了好久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是受到了一些伤害的。”
李宇春曾这样形容人群带给她的自我的剧烈收缩;但这与她刚刚同我说的“一次性表演中与观众的近距离”对她产生的诱惑,形成了一种非常生动的互文。
我在想,人群之于李宇春,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像海水之于鲸鱼,是一种界限并不模糊的包含关系。海水,是鲸鱼生命最根本的养分,但也是它生命最深层的威胁。
这是自然规律。越脆弱,越美丽。
我没有忘记李宇春首先是一个歌手,于是我问她,对她来说,音乐的表达和表演的表达,区别是什么?
我是2019年去的《演员》,我当时做了一张专辑叫《哇》。做完那张专辑之后,我一度感觉我没有释放完。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始终还是在一个流行音乐的范畴里表达。流行音乐归根结底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作为流行音乐,哪怕你把一首歌做得再长,做到五分钟、八分钟,它的表达还是受到了篇幅的限制。
当我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是歌手李宇春在表达,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不会去想那个歌曲本身有什么表达,他们只会觉得好听或者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表演不太一样。它可以通过你塑造的角色,去讲出你心里的话。可能对于这种更隐晦的表达,观众更不易察觉,但你隐藏在人物背后的那种感受的确存在,而且空间上更大。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音乐无法实现的。
“那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流行音乐的表达更显性,表演艺术的表达更隐性吗?”我追问。
李宇春并不掩饰她的包容性:
这么讲也没错。
“在这当中,审美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吗?”
审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
我曾经听过一个描述,说演员、歌手这类职业是没有什么创作成本的。但是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你在某时某刻的想法或者说你的审美,它其实是通过你过去大量的投入所积累起来的。这个投入就是你的成本。它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去计算,但是它很重要。
形容程度的时候,她喜欢用“很”“非常”,很少用“最”“超级”。
02
“你觉得你有天分吗?”我问。
这个问题更完整的表述是,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是李宇春并没有天分,她只是被时代或者命运所选中了。
天分…...
李宇春念了念这个词,琢磨了一下,随后语速很快地、腼腆地回答道:
我常常觉得我没有,我常常觉得…...我没有。
她倒没有想很久,而是重复了一次,表情里立刻闪烁起一种不稳定的生动。
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有一些些,当我的感知就是比别人要细微,或者说更易喜易悲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好像是我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没有可能你的天分就是你的性格?”
这一次她思考得慢了一些。
我觉得肯定是跟性格有关的。因为它能够帮我去吸纳营养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性格很重要作用就是它会帮助我做出一些决定。
每个人因为性格不同,他们的决策是不一样的。
人人都在问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她关于性格的这个回答已经非常接近答案了。
“你有过后悔的决策吗?”我继续问道。
有过不够好的决策, 谈不上后悔。
“你追求完美吗?”
我小时候更加追求完美。现在反而不。
“现在能够更好地跟瑕疵相处了?”
一方面是相处,另一方面是我越来越感受到了一些失控状态之下产生的新的灵感,或者是刺激。
“失控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吗?”
我以前不觉得是,因为以前我是什么事情都要安排好的,要让事情处在我的掌控范围内。我也不喜欢去party,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很尴尬之类的,但我现在有一种新的体验。
比如说有的时候出现一种尴尬的场面的时候,我会更多地去观察,因为我想知道那个尴尬的局面是怎么结束的,或者是…...看谁先迈出那一步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失控会让很有趣的东西出现。
而且因为我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安全的区域嘛,那么,假如说,突然有一次我不是在一个安全区域里,或者是临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在你(我)手足无措的时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记忆很强烈,因为我会觉得它可遇不可求,因此它也很珍贵,你会想要留住那个痛感,所以它实际上可以帮助我写出一些你无法复制的东西…...我尽量表述清楚。
李宇春说话的时候,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她用词并不总是很准确。尤其是在形容一些抽象的感受时,她会把她的感受清楚地传递给你,但是这并不体现为字面上的精打细算。
另一个是她从不皱眉。一是一,二是二,来往利落,情绪平稳。
前者体现真诚,后者体现洒脱。这一切都引导着我相信李宇春身上依然保存着某种纯洁性。
“你是否有精神洁癖”?
我相信我有。
我得再补充一个特点。
她说话,永远不会表现得全知全能,即便说的是自己的事也是一样。你可以说她是小心翼翼,也可以说她是以退为进。
“因为你歌词里时常写到纯白、纯洁之类的词语,那么我想知道保持这种纯洁,它的代价是什么?”我懒得再绕弯子。
我觉得那只是我某一方面的一种理想主义。
我肯定是有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而且这种理想主义在跟现实碰撞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稀烂。
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下一次孕育我的理想,不会影响我对于理想主义这个东西的信任或者是对一个事情的判断,或者对人的一种态度等等。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李宇春)认为李宇春比较可贵的地方。
李宇春在我们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就告诉我,她经常用第三人称的姿态来跟大家讨论李宇春这个主体:
我常常会跳出李宇春去看李宇春。
有的时候我跟同事聊天,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会说我觉得李宇春怎么样之类的,当然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但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怪,什么叫我(李宇春)觉得李宇春xxxx,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去看。
我不会过于呵护她,我也不会过于刁难她,我只是用这个视角去做一些判断。
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跳回去的时候,会很可怕!
“为什么?”她说很可怕的时候,的确露出了一个被吓到的表情,我咯咯笑。
这就是我跟同事之间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在决策某个事情要不要做的时候,我常常会跳出来讲,我认为李宇春应该怎么样,我跟他们讲完之后,我就跳回去,这时候,我就是当事人了,事情就变成我是李宇春,他们说我应该怎么样,作为当事人,我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跟自己打架。
“谁赢得多?应该是跳出来的比较多吧。”
她也赢过,但是也有那种情况,就是情绪真的抵触到了一定份上了,就是不想干。
“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你会特别沮丧,你会受到伤害,你会…...怀疑这个世界,你甚至会产生对人性的某种失望,你也能感受到现实世界里很多东西的无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现实题材电影的原因。但我觉得还是能够比较积极地,也不叫积极,是正常,我觉得我也谈不上积极,就比较正常地、比较真实地去接触别人。
“什么叫做正常?是一种被社会规范的认知吗?”
我说的正常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
我看有一些人的生活状态、他的轨迹或者一些宣言等等,我会觉得好积极,跟那些人相处起来,我会不会太丧了?但实际上我知道我也不算是丧,所以我就是把它归于正常的一个区间里。
有时候,我会感受到现代社会存在某种功利性极强的精神哄抬。不论是对正义,还是对平等,或者是对自由、对仁慈,某些言论都呈现出一种非常暴力的姿态。
它要求你必须积极。
李宇春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缓的可能。
“你比较喜欢哪个导演的电影?”我问她。
她想了好一会儿:
像法哈蒂的作品,我就蛮喜欢的。
除了他的故事本身之外,其实我觉得他会带到环境,或者说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底子,像这样的故事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还有,他的作品里有一种深深的为难。包括《一次别离》、《推销员》等等,它就是让你觉得,好为难,每一个人都…...好为难,可能这也我喜欢这样的电影的原因。
我明白法哈蒂刻画的那种为难,但是我并不理解李宇春的为难。
后来她讲了一个别的事情。
我在之前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环节是要面试别人。我也很不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
就是他如果选择了你,你是接纳他还是你觉得不合适,你要去拒绝他,我不知道。因此,他反而像一个面试官。我的确有一些生活上的空白,我没有办法。
我思考着她说的。
我应该也没有办法…...跳槽吧,应该没有办法跳槽。
李宇春补充了这句。
03
当大家谈论到李宇春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好像都会从2005年谈起。
“16年过去了,还是这样,这会让你觉得有点乏味吗?”
会有一点,说实话,会有一点。
李宇春说这话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是人们对于时间本身有一种感情吗?”
我觉得是一种记忆,那个记忆很难磨灭或者更新。不光是认识我的人,包括我的妈妈,她有的时候也会聊到05年的一些事情什么的。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深刻很深刻的记忆吧。
“你本人去回看这种记忆的时候,会觉得很遥远吗?”
我倒没觉得很遥远,可能因为我常常会问起,这种记忆并没有被尘封起来,反而常常会被人唤醒,大家会去问某一个故事或某一个细节,所以我觉得它在我脑中是活跃的。
我对于2005年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探索的兴趣,因为我没有任何办法去了解它在人们的脑海中存在着怎样的变形。
我只是问她如何去适应那种剧烈的变化的。
我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个自闭的过程。
“自闭?”我试图抓住这个词。
对,非常自闭的过程。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聊天,但我以前是不可以的。我以前没有办法做到。
我没有办法非常放松地去描述我的一些感受。媒体问我一些问题,我会非常的紧张,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是或者不是,除此以外就没有更多的表达了。因为当你处在一个不单单是被关注而且是被质疑的这样一种不友善的状态的时候,你自己其实也会收紧,然后你会有一层壳,就是这样子。
“这种自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我其实有将近10年的时间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我的同事有很多其实是从05年就开始陪伴我的,他们看到了整个过程。
因为昨天我们刚好拍芭莎,我们有一些新的尝试,所以我也刚好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以前一直是他们在推着我走。我这个也不想碰那个也不愿意摸,我只想做音乐,可是很多东西他们会推着我走,因为他们希望我走出自己那个小空间,走出自闭的状态,然后可以伸出触角去感受不同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这么高尚的理想,但现实是这样。
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有很多现在的东西是我主动在选择,而且有的选择会让他们大跌眼镜。
比如说我最近录的节目,我可以撕开自己的伤口,去面对曾经的一些伤痛,甚至昨天晚上我们尝试的那个很奇怪的妆容,我突然发现在say no的是他们,反而去尝试的那个人是我。
“因为你变勇敢了是吗?”
我觉得勇敢只是其中的一小点。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你看过更大的世界,你感受了很多人创作的那种过程,你会被吸引,然后它会带给你一些创作欲望和兴奋感,你的内心变得更加丰满了,你渴望去做这样的尝试。
诚实地说,我从现在的李宇春身上看不到任何自闭的影子。
也不像采访前大家知会我的那样,她会流露出任何生涩或者拒绝,反而她的状态我觉得可以用干练来形容。
我细细地思索着“李宇春自闭的那十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坐在李宇春身边,每一件我好奇的事,我都可以爽快地问她。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她不肯回答而已。但是唯独这个问题,我问不了,因为她也回答不了。
时间,总是以一种麻醉剂的姿态抚摸着人们身上的疤痕,让曾发生的伤害看起来都处在一个渐渐痊愈的过程中,直到那疤痕渗进我们的灵魂深处,失去了物理上的痕迹,人们从此也彻底失去了证明伤害存在过的证据。
因此,谁也无法恰如其分地形容被时间改造过的袭击与痛苦。
甚至没有人愿意主动铭记它,只是出于诚实,我们也没有选择遗弃它。
最终我在李宇春跟我分享的一个纪录片里,找到了“那十年”的影子:
我最近看的一部纪录片叫《我的章鱼老师》,它其实就是关于生命的一个议题,但是他用了比较轻的一种方式去讲述,这部纪录片是我最近流泪的一部。
它其实就是讲一个人跟章鱼之间的事情,但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主人公刚好处在人生的一个瓶颈期,于是他就去拍一个章鱼,因为章鱼的一生很短暂…... “鱼生”很短暂,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他跟这个章鱼相处,看着它怎么去猎食,怎么去躲避,怎么去度过它短暂的一生。
章鱼向主人公伸出触角的那一刻,我流泪了。
我在听李宇春讲述这个片段的时候,也有一点动感情。因为我明白,她说的实际上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生物,同时处于一种拥抱世界的渴望和犹豫之中,最后对彼此产生了依赖与情感的故事。
人们会为此流泪的原因是,拥抱世界,太难了。
不是因为世界有多残酷,不是,而是因为世界它本身是一个过于丰富与未知的概念。是我们自身太脆弱了。
我流泪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是我在疫情发生之后看的,我的情绪会(因疫情)更不一样。
“你对于疫情的具体的感受是什么?”
2020年的整个上半年,我是比较沮丧的,我受到了很多情绪上的打击,在上一年,我写《人间乐园》的时候,关于环境保护、人类文明的一些东西,我是思考过的,但是疫情让这一切这样啪地、猝不及防地展现了在我的面前,它是关于那些命题非常具体和生动的表现。
那种被撞击的感觉,特别强烈。
“因为人类是一个很宏大的词,但是在去年它变得很具体,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宏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可能让它变得不空洞呢?”既然她提到了人类,那么我也希望我们对此的探讨不要是一种简单的自我标榜,所以我追问她。
对此,她显然思考过,但是还没有一个结论。
很难,这一点非常难。
用一种比较浅显的语言去表达一种很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它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讲人类的这样一个命题。
首先它切入就很难,然后每个人的理解诉求又会很不一样,要照顾到受众的广泛性它又很难;或者你还想留白,还想留给听众一些空间,让他们去想象…... 这是跟你单纯表达自我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当时在写《人间乐园》的时候,我觉得它就连一个小众的歌曲都算不上,它就是我自己臆想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尝试。
“你的这种更大的创作欲,实际上是使得李宇春更完整了吗?”
它是成长带来的,就像章鱼一样的,当那个环境没有那么恶意了的时候,它会愿意去伸出触角,它会愿意去感受。
你们看,在这样的语言碎片里,我们还是足以瞥见“那十年”的影子。
它不需要被深挖。
因为在某个维度里,过去是不会过去的。
过去是被雕刻在我们每一个若无其事的笑容里面的。
我一直都认为我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慢,也不是所有的都慢,有些时候,跟同龄人相比,我好像又比他们要冷静,要成熟一些。但也有的部分,我就好像生长得比较慢。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挺矛盾的。
比如说当你突然被关注,突然有很多人涌向你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封闭状态,你会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你可能有不安、有怀疑、有蒙圈,我不知道一切是为什么发生,所以其实就好像处在了一个真空状态。
但是当这一切开始变得温和一点点的时候,你打开自己的那个世界去感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我好像比任何人都要敏感,我好像会比别人感知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些东西会成为你创作的一些小种子或者养分,你就会希望可以打开更大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说的慢,是因为它有一层封闭的时间,可能那个阶段我是没有去汲取的,但是好像打开之后它又变得很快。
李宇春那天跟我说了很多。
她有时候说得很详细,有时候又很简短,有时候说得很快,有时候又会被一个问题打入思考中,自言自语“我怎么没有这么想过”。
我阅读着这样的李宇春,感受到的是较之2005年的她大得多的自我和自由。
最终我还是问了一点点跟2005年有关的问题。
“即便李宇春已经离开2005年很久了,但是别人依然用一种符号化的眼光,在看待你,它们称你为偶像。你作为这个符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感受…...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成长了,而很多人停留在过去?
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去想,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在意每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你控制不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想了,我没有时间去逐一地在意这个东西。
客观来说,我很多东西是在往前走的,我也很想往前,所以我没有去过多地关注这个事情。
“这个里边是不是有可能存在一个相对悲观的事实,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的认知都是在主动成长的?”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她认同了这个事实。
这是正常的,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为难,有自己的委屈,有自己不如意的一些东西,当你越观察别人或者是越关注很多社会层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这一点委屈,是微不足道的。
她也解释了自己的豁达。
一切表达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显得很得体。
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一个人。
那是《三体3》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叫云天明。书中有一段关于他的描述,是这样的:
“云天明在程心的记忆中是另一个样子。在阶梯计划的那段时间,一个憔悴虚弱的绝症病人;再早些时候,一个孤僻离群的大学生。那时的云天明虽然对世界封闭着自己的内心,却反而把自己的人生状态露在外面,一看就能大概知道他的故事。但现在的云天明,所显露出来的只有成熟,从他身上看不到故事,虽然故事肯定存在,而且一定比十部奥德赛史诗更曲折、诡异和壮丽,但看不到。
三个世纪在太空深处孤独的漂流,在异世界那难以想象的人生旅程,身体和灵魂注定要经历的无数的磨难和考验,在他的身上都没有丝毫的痕迹,只留下成熟,充满阳光的成熟,像他身后金黄色的麦子。”
基本上,这就是我对于李宇春的感受。
我常常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所以你我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己的生命的客人。
我们都是来做客的。
只是,生命有时也对我们招待不周。你分不清它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你只是不得不去在这次拜访中反客为主,这样你有机会照顾好你与生俱来的捉摸不透的灵魂。
你分不清这是考验还是奖励。
很多很多时候,你只是不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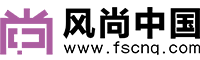
 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